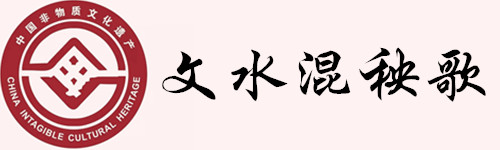文水混秧歌,即南关混秧歌。南关混秧歌,历史悠久,据推测始于明代。明末清初形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活动,在过大年和过元宵节以及老百姓祈雨和喜庆丰收时最为活跃。很久以前,文水民间接麻衣仙姑时,有十八村的“红火”参加,其中著名的除了岳村鈲子和桥头大鼓外,就有南关村的混秧歌,在表演中十分引人注目。
南关混秧歌,它是一种不用固定舞台,随时随地可灵活地打地摊表演的民间“红火”。所用乐器有一面铜锣、一个响环、一面旋转旱伞、数面腰鼓、若干镟子和手锣、铙钹、水铰各一付。
演奏时,每人一件乐器,由铜锣开头,响环指挥,大伙围成一圈敲打。队员们头上裹着羊肚子白手巾,腰上拴着红绸腰带,演奏起来手舞足蹈,非常热闹。演员们最喜欢四六句表演,因为闹混秧歌唱词都是四句或六句,所以叫四六句。
后来在演唱实践中,也常有人打破这种传统格式,使之适应于内容需要,可长可短,运用自如。“四六句”保留了锣鼓曲中的欢乐部分,在说唱中发展了它具有曲艺特色的抒情部分,使之能够表达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感情。表演时唱词多为即兴发挥。
队伍里有上装扮相的演员。常常是刁泼霸道的老太太,“她”头戴洋钱边帽子,耳朵上挂着两个大红辣椒,用写春联的大红纸印两个红脸蛋儿,手里挥动着一把扫炕用的扫帚,扭起来总是跌跌绊绊。那双无法装饰的男人大脚和那张极力扁着的嘴巴,使其扭捏作态显得更加深动形象。有时是饱经沧桑的老头,他头包白羊肚子手巾,胡须上粘着特别夸张的假胡子,本已很深的皱纹上又重重画了几笔。他手握一个大烟袋,罗锅着腰,踩不上节拍的舞步,尽显其一肩的负担和一脸的愁苦。有时是滑稽可笑的丑公子,他头戴高筒毡帽,翻穿羊皮皮袄,两脸颊涂成白色,手举一个硕大的鸡毛掸子。鼓声一起,他总是蹦蹦跳跳最先上场,绕着圈儿把表演场子打开。正式表演时,他也没有固定的走位,跑动中,他一会儿模仿孙猴子,一会儿模仿猪八戒,表情和动作里透着灵气和智慧。这三个角色可以说是秧歌队的丑角儿,其动作要多夸张有多夸张,要多可笑有多可笑,每次表演都不尽相同,全凭他们临时发挥,在场子里随意地扭动、蹦跳,像流水一样,看似无形,实则有势。
当秧歌队伍某某字号时,歌手们即兴唱道:“某某字号真是好,金马驹儿驮元宝。驮元宝驮元宝,驮上元宝往进跑”。有触景生情即兴演唱的,如看见一串红花纸时,就唱:“初四四,十四四,抬头看见红花纸,红花纸,红花纸,写的四个黑字字”;也有带风趣味道发笑的,如:“初六六,十六六,天上飞的丢溜溜(即老鹰),丢溜溜,不习好,屙下祖宗一得脑(头)”。“高高头上一株柳,年年割了年年有,有一年,没啦割,一下长了桶儿来扑(音po,粗的意思)”。也有瞎唱的,如:“正月十五闹哄哄,瞎子拐子来观灯,瞎子观灯不见明,拐子走道地不平。”又如:“初九十九二十九,提上凉袜打烧酒,掌柜嫌我凉袜臭,打上烧酒水不漏。”
闹混秧歌唱四六句,不但专门的歌手唱,观众也有抢着唱的。不仅大人们可唱,就是十来岁的孩子也可以唱,唱词多用方言土语,朴实无华,极具地方特色。
南关混秧歌最动人的场面是响环、腰鼓、四六句、过街板有机结合紧密配合,令人兴奋不已。响环是专门打节奏,也是乐队的指挥。持响环者劲头实足,全体乐队队员都得听他的指挥。南关村民王绍杰(人称“放羊五”)是持环的好手。再一就是腰鼓手,有时两个有时一个,在队伍的圈子里游来游去,他们打得快慢,队伍随即跟上他们的节奏,打到高潮时,腿向前一跨。乐队就跟着他停下来。这时歌手就唱,唱完再打。南关有个李生(人称三虎儿),是打腰鼓的好手。武德玉、王清林、四成儿混秧歌唱得最好。武贵荣、武宝荣的铜锣敲得最佳。闹混秧歌需要有个头儿,武根年是村里闹混秧歌的领头人,他还有一手打镟子的好功夫,人人喝彩。
“过街板”的唱法,有独唱,有对唱,还有多人唱,表演者灵活机动,随着乐队的音乐节奏,唱人物,表故事,抒感情,内容丰富,简洁完整。如“诸位同志不要吵,听我把三个女婿表一表:大女婿一脸疤,二女婿疤渣渣,唯有三女婿生得好,秃头上没有一根毛,三个女婿都来到,你看热闹不热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关混秧歌搞得更加活跃了。逢年过节,慰问军烈属等都要在南关村和文水县城里大闹红火,吸引来许多观众,给节日增添了喜庆气氛。
南关混秧歌到清末民国初期,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其传承人有杨万保、武春金、武占鳌和“二补脑”等。到了民国期间,韩四牛、杨成儿、王绍杰、马连根等人继续发展传承。新中国成立前杨旺、李生、杨德胜和韩玉等作为传承人。五十年代传承人有武根年、高德福、武德玉、王清林、武贵荣、武宝荣、武万生、武恩德等。六十年代后传承人有武占海、李树贵、赵吉生、武全维、武士文等。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南关村的刘旺昌、马培深、武永维、刘汝昌、武安维等作为传承人,他们将南关混秧歌改为文水混秧歌申报,经批准,文水混秧歌已被列入文水县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项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