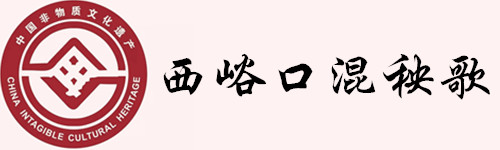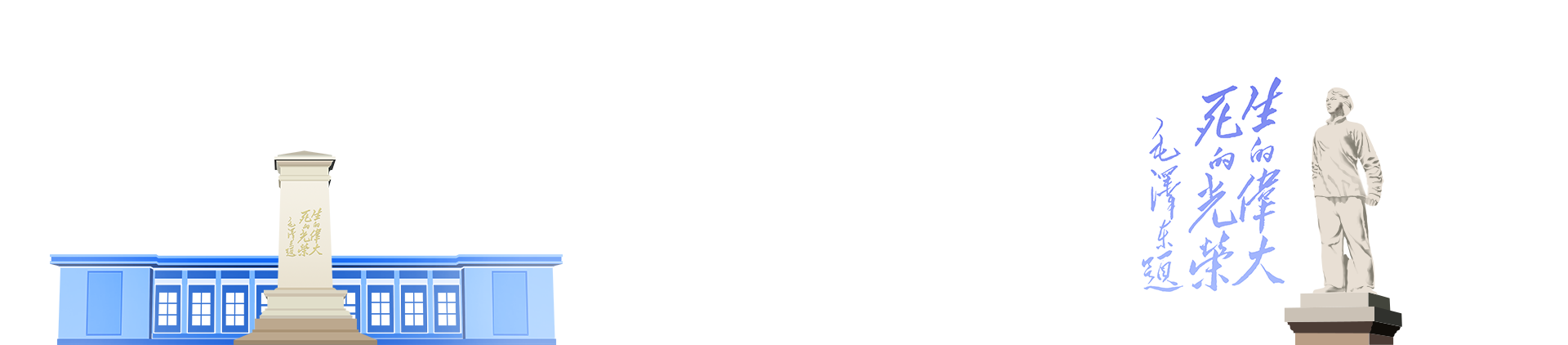西峪口混秧歌是活动在山西晋中一带的街头文艺形式之一,始于明末清初,有近三百年的历史。形式简单,易于表演,深得群众喜欢。表演内容以梁山人物故事为基础,因此也称“西峪口梁山混秧歌”。它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三十二个阵式变化,引人入胜,赏心悦目。混秧歌的乐器响起,铿锵悦耳,声震山岳,各种乐器配合有致,是一种难得的击打协奏乐,效果特佳。
相传早在明万历年间,山西晋中一带的人们,凭着丰富的经验,运用智慧的心灵,集体创作出了晋中秧歌。由它派生出了一种能在街头表演的秧歌,就是混秧歌。它活动的范围波及到吕梁山麓、汾河两岸,而重点却在文水的开栅和交城的广兴等地,其中西峪口与这两地紧邻,该村混秧歌被人们广泛认可。
西峪口原是个山清水秀、风景诱人的好地方。它的西北方向有个海拔500米小山梁叫神头岭,别看它小,却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产之一。开始这里仅有姓曹和姓冯的两家聚族而居。明万历年间,遭灾大移民,这里先后来了姓刘、姓郭、姓宋的三大姓和姓康、姓姜、姓王的三小姓人家,其中姓刘的名叫刘希望,他有四个儿子,分别叫刘兵、刘将、刘军、刘官。在这个刚刚组建的不满百人的小村子里,刘姓人口酷爱文艺,其三子刘军是杰出的的文艺骨干之一,他能歌善舞,富有组织才能。他跑遍附近的乡村田间,收集了大量有关混秧歌材料,在此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终于使西峪口混秧歌红极一时,名震南北。
混秧歌的队伍有伞头、耍弓子、打腰鼓、磕棒子、击镟子、抖大杉、敲马锣、丑老汉、丑老婆等三十二人组成。
伞头两名,有正负之分,负责全队伍的指挥工作。队伍的移动、阵式的变化、乐器的响止全凭伞头的伞、耍环、哨子等指示,他让动就动,让停就停,让快就快,让慢就慢,整个队伍的移动进退,乐器的轻重缓急,都在伞头的掌控之中。据传正伞头代表宋江,负伞头则代表卢俊义。
腰鼓手有八名。腰鼓是混秧歌的主要乐器之一。腰鼓手要求精悍利索,具有一定的武功。特别是头架鼓手,是队伍行进与阵式变化时与伞头配合最重要的人员。他的一招一式都为后面队伍起着示范作用。腰鼓手代表梁山武功高超的八个马军头领。
磕棒子有四名。木棒长约二尺,粗细以手握住为宜,由坚实的响木制成。磕棒手鼻部画石榴、青蛙等图案。击棒时,上下左右翻动击打,令人眼花缭乱,顿生敬畏之意,是行进攻守的主要人员。磕棒手代表梁山的四个步军头领。
击镟手有八名。乐器为铜镟与木匕首。一般由女性充当,代表梁山的三个女头领与武功较弱的五个步兵头领,在乐器的击打过程中,主要配合伞头的耍环掌控节奏。
抖大杉有四名。代表梁山的吴用、公孙胜等文职人员,是梁山的智囊团,起着出谋划策的作用。
耍弓子有两名。这是队伍的中级指挥人员,也可叫作二架伞头,代表梁山的花云与燕青。
丑老汉、丑老婆各一名。丑老汉腰插大烟袋,拄着拐杖;丑老婆手摇羽扇,在队伍中进退扭捏,十分逗人喜爱,是梁山消息传递员,代表戴宗与时迁等。
西峪口的混秧歌跑场子有三十二个阵图,这些阵图有的相生相克,有的环环相扣,真可谓变化无穷,变幻莫测,实乃古人智慧之结晶。
纵观阵图,最大之特点就是一个“转”字,一个“变”字。有的正转,有的反转;有的直转,有的斜转;有的单转,有的复转;有的四角转,有的中心转;……转中有变,变中有转。如二龙戏水转:两个伞头各带一支队伍,先在四角转后,再到中心转,宛如两条巨龙在水中戏耍。又如四门阵:队伍在东南西北四方成弓形而在中间旋转,转成四个门洞。如将敌陷入阵中,非从四门出入,才可进出阵,找不到四门则无生还。再如十门阵:四角旋转成四环,各在中间成8字旋转,三次成六环,合为十门。此阵也可叫十面埋伏阵。还如闯乱营:两队同样是从四角旋转,但一队是在中部转后直插偏下方再成斜“8”字方向下方转,中间相遇后,重复对方所走过的路线行进,这样两队就在阵中央形成乱中哆嗦之势。
阵图的形成确系古人勤劳智慧的硕果,并非一朝一夕之功。纵观三十二阵图,有的符合对称之规律,有的与太极八卦相吻合,身临其境,会使人眼花缭乱,心旷神怡。
西峪口混秧歌出去表演时有一定讲究。
在主客会场时,即两村的混秧歌会到一处时,主方要到村口迎接,这场面是非常壮观的。双方的伞头要用伞三点头行拜见之礼,经过激烈的敲打会拜之后,在主方的引导之下,把客方迎到村中,接着双方要在较宽的街道上进行竞技表演,主要是声音与形体动作的比拼。休息时,主方要用烟、茶、糖、水果等热情招待客方。客方返回时,主方同样要列队送到村口,并行送别之礼。
在冬闲节日跑场子时,即混秧歌的活动时间,主要集中在冬闲时的正月。从正月初六到正月十四是跑场子的日子。届时在宽敞的打麦场上,或较大的院内按阵图进行演练。练到热闹处或焦点时,偶尔有推迟吃饭的情况,即使废寝忘食也心甘情愿。
在本村和出村拜客时,他们的拜客时间从正月十五到正月十八,分本村拜与出村拜。本村过去是拜村公所与村里有名望的人,现在是拜村委会、军烈属、企业家或盖房、生子等喜庆人家。谁家想让混秧歌表演,就在自己家门口放礼炮。进院后边敲打表演,边说唱些吉祥喜庆的顺口溜与快板。主家要用喜糖、喜烟进行答谢,然后热情送出,从而增加村民之间的和谐之美。外村拜客与会场相同。近几十年来,还要到驻地机关、单位拜访,更增进了双方的友谊与团结。
几百年来,在混秧歌这一文艺领域,出现过许许多多的奇闻轶事,下面摘录几则以示西峪口混秧歌的文化底蕴。
曹杰力扶台柱:民国元年,西峪口混秧歌到交城广兴表演,由于人多加之后生们的起哄,搭起的台柱断折了,伞头曹杰一把抱住了断折的台柱。既保住了戏台的安稳,也震慑住了起哄的小后生们,一时传为佳话。
宋万金技压群雄:民国三十四年(1945),文水举行抗战胜利庆祝活动,各村的红火都到县城表演。西峪口村的混秧歌进行了精彩的表演。最突出的是头架鼓手宋万金(亦名宋斌),他一会儿黑叫驴打滚,一会儿柳树盘根;一会儿仙人指路,一会儿海底捞月;一会儿燕子取水,一会儿鸽子翻身……他的演技赢得了不断的掌声与叫好声。
姜飞虎一石成名:相传百余年前,西峪口村出了一名大侠客,名叫姜飞虎,他身体强壮、武艺高强,也是当时村混秧歌的伞头。一次在二郎山下的河滩中,有一块近400斤的大石阻住了洪水,眼看就要淹坏附近良田,在场的许多人想方设法也无济于事,正好飞虎路过此处,人们久闻他力大,劝他相帮。他说怕毁了他新买的鞋。大家说你除掉顽石是大事,鞋是小事。飞虎下河滩后,双手紧抱,一声怒喊,石随声起。人们看时,他穿的新鞋,底帮分开,针线全断了。他的举动惊服了众人。
西峪口的混秧歌自组建以来,经历了多次的传承与发展。在历史的变迁中间,有时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忽而又跌入低谷。过一段时间,又可攀升到新的高峰。
从刚组建到义和团运动时,混秧歌赋予了梁山人物的故事,这是第一个高峰。当时抵抗外来民族的入侵,中华民族急需要一种自发的反抗精神,这时油然而然滋生了梁山农民起义的火种,混秧歌就有了它的历史责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日寇的铁蹄下,混秧歌的主要人员遭到了屠杀,一些宝贵的资料遭到了焚毁。如三十二阵图就烧掉了八阵,仅存的二十四阵也是残缺不全。这时,混秧歌又陷入了空前的低谷。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指引下,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经过多方努力,损毁的三十二阵图得以完善,特别是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文艺骨干后,混秧歌发展又增添了新鲜血液。就以伞头为例,早在百余年前,最有名的伞头有刘吉万和曹杰。到了解放后,出现了郭本有、郭本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刘树龙成了较有名气的继承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刘模儿、巩肉小、郭成林这些新秀担起了传承人的担子,成了西峪口混秧歌的“顶梁柱”。
经过多年的传承发展,西峪口混秧歌已经被列入文水县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项目行列。借助政府的扶持,它必将枝繁叶茂,硕果累累。